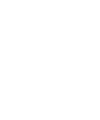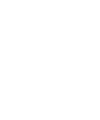地煞七十二变 - 第一百一十章 祖师
天未明,夜未央。
兰立坊高高垒起的三层祭台上已是熙熙攘攘,提前赶来的信徒们簇拥在台下的巡神道旁,或诵经祈福,或焚香祷告,沿途,经声掀动沿街旗帜作云雨,香气熏蒸树上彩绸换新春,就这么,富贵繁华、热热闹闹,一路穿街市,跨桥樑,直抵轮转寺脚下。
寺前,长长的石梯上亦有信徒簇拥,一眼望之,儘是被朱佩紫之人,却都恭敬侯在两侧,留著中间铺著厚而软的西域毛毯沿阶向上,穿过巍峨山门,直抵堂皇大殿。
殿前广场中央,佇立著一副由莲台、神轿与宝盖构造的华丽鑾驾,守山大神宝光天王背悬宝轮侍立一旁,四万一千眾的护法兵將若隱若现拱卫周遭。
四下又大张灯火,烛照广场如白昼,寺內大小僧眾皆著锦绣法衣、修仪容,或提香炉,或举经旗,或捧乐器,个个昂首挺胸神情激动一副跃跃欲试模样,却又规规矩矩默默肃立当场。
他们在等候著,或说整个钱塘都在等候著。
舞台已垒成,观眾已就位,鼓吹已备好,静待主角登场。
“报!”
急报声伴著一道流星直射广场。
“大胆。”
神轿旁,宝光呵斥一声。
“岂敢衝撞法驾?”
背后宝轮放出佛光,当空一刷,顿將流星定住,现出形状,是个神情慌张的耳报神。
“出来了!”
“什么出来了?”
“城隍……不,偽城隍出来啦!”
“什么?!”
宝光心底才“咯噔”一跳。
噔~是骄矜的和尚心惊误拨了琴弦,噹~是昂扬的僧人胆颤失手坠了提炉,宝光眼角扫过群僧,各有各的慌乱,连门口都有信徒探头张望。
他忙收敛神情,笑道:
“我当是甚大事?许是那李道士终於晓得自不量力为何物,没脸皮见人,趁夜回他那飞来山……”
话声未落。
又一道急报传来。
“报!偽城隍人马往本寺来了!”
场中终於按捺不住,惊呼譁然一片。
宝光也顾不得佯作轻鬆,连声追问:
“巡逻的人马呢?怎生不加阻拦?”
“打头的恶神凶焰滔天,煞气一衝,巡逻人马就散啦。”
“好贼子!他们出动了多少人手?有哪些头目?”
“凶气太炽,瞧不真切,约么有百十人鬼。”
宝光脸上阴沉,口中喃喃:“这帮妖贼,真敢动手不成?”
他虽眼高於顶,视窟窿城为野鬼,瞧城隍府为毛神,可城外那被从山峰碾成台地的飞来山,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著他,窟窿城如何凶,能捣毁它的城隍府又该如何恶。
心底急转。
轮转寺护法兵將有四万一千有余,当然那是对外宣称,实际能战之士有四千出头,而轮转寺与其余十三家不同,因荷负阴阳重任,大部人马向不外调……
“宝光,戒痴戒嗔。”
忽有细语如清风拂过广场,场上僧人霎时如迎风细草,纷纷伏倒,口呼“祖师”。
可瞧那徐徐步入广场之人,並非僧人打扮,而是著玄衣、戴冕旒,腰束金玉带,手把玉如意,儼然人间王侯模样。
那王侯或说妙心禪师,到了大殿前,招呼报信的护法神兵匍匐上前。
“他可曾踏足巡道?”
神兵一怔。
“不曾冒犯。”
方向都不同,哪里挨得著?
“弟子们性命可有毁伤?”
“亦无毁伤。”
弟兄们跑得快,都没咋伤著。
妙心听了,唱了声“阿弥陀佛”,抚须向眾僧笑道:
“原以为那李道人来歷不明,又喜与妖鬼为伍,是个贪婪残暴不晓道理之徒,混世魔王之流,不想也有几分佛缘与悟性,不枉本府赠他书信一封,渡化一番,果然立地成佛。”
周遭僧眾听了,都讚嘆祖师果然佛法无边,竟能化此凶顽,磕头磕得越发诚恳。
宝光也恍然。
城隍府那帮凶神恶鬼虽悍勇,却又不呆傻,怎会以百十人鬼来衝杀自己手下四万一千余部眾?而此时前来,既不是为挑战,那便是为投诚。
心底懊恼。
一时慌张,竟叫老禿驴又踩著自个儿出了风头!
面上愈发恭敬。
“宝光惭愧。”
至於老禿驴,不,妙心禪师微微頷首,没急登上神轿,只回身凝望著大殿。这间佛殿以规模与雕饰看,足以比肩帝王宫殿,然牌匾上却空无一字,神台上也空空如也,却是座空殿。
寻常寺庙道观,除却所供主神,多有其余神佛陪祀,但轮转寺不同,建寺之初,只是存放明行成祖师金身的祠堂,后陆续扩建,也只是为供奉明行成歷代转世金身,而后更成惯例,寺內除了明行成的金身蝉蜕,不供一神一佛。
也因如此,在数百年前,钱塘高僧大德们重新厘定阴阳之时,特意选定轮转寺来掌管轮迴,毕竟,一些个大事要事实不足为外人知晓,哪怕是高居九霄云外已久不视人间俗事的神佛。
至於明行成祖师?一个千年前的传说与那龙君的故事一样,何其虚无縹緲。
理论讲来,轮转寺实是明行成的道场,而明行成亦是寺內眾僧与眾神將唯一的宗主。
所以千年以来,只教万家香火熏了几具乾尸枯骨,偌大的佛殿留给了空无一物的莲台宝座。
而今,这几百年的空置终於要结束。
妙心目光幽幽。
待他登上城隍宝座,还有什么地方更適合作为新城隍的治所?轮转寺是他的寺庙,是他的道场,又怎能奉他人为宗主,唤他人为祖师?!
心神暗暗激盪之际,又有传报。
“偽城隍已至山下。”
宝光天王恭声请示,妙心却好似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没有半句回应,宝光於是会意:“叫他们在山下候著。”
一贯的傲慢,妙心听在耳中,毫不在意。一介孤魂野鬼、手下败將,已不值一提。看在他冒认城隍,为自己开了个好头的份上,若等会儿言行足够恭敬,將来撤去明行成金身后,赏他一座偏殿容身也未尝不可。
他昂首望天,天上莲池黄中染青。
可惜,那十二个老鬼实在不识趣,在这重要日子,不肯让轮转寺晨钟独鸣。
以后且来计较!
他心底冷笑,张开双臂,便有隨身服侍的天女上前,搀扶著他飞上神轿。
而后低眉垂目。
静侯著……
咚~~
悠远钟声伴著佛音裊裊。
“譬如长者,有一大宅……”
咦?今儿是封神的日子,怎生奏的不是礼乐,却是佛经?
妙心禪师诧异睁眼。
抬头瞧,东方天际未白。
低头看,僧眾面面相覷。
谁鸣的钟?谁唱的经?
…………
山下。
钟响之前。
“祖师有令,叫尔等在此等候。”
一队护法拦住前路。
刚照面时,这些兵將先前还是战战兢兢如临大敌,可当城隍府一方递上拜帖,表示无意武斗,却忽的又拿起了鼻孔看人。
李长安懒得理会他们,回头道:
“和尚,交给你了。”
人群里,法严仍旧是那副潦草模样,他双手合十,唱了声“阿弥陀佛”,不多言语径直上前。
踏上石阶的第一步,却好似踏上了音阶。
咚~~
钟声在黎明前夕迴荡。
伴著佛唱裊裊:
“……其宅久故,而復顿弊。”
“堂舍高危,柱根摧朽。
梁栋倾斜,基陛隤毁。”
佛音渺渺传递入轮转寺后山一座偏僻小院。
院里厢房的床榻上,僵臥著一个脸颊清瘦的和尚,仪容整洁,面容红润,可若贴近,却听不著一丝呼吸,仿佛死人。
床榻下,蜷缩著一个小沙弥,脑袋一点一点正打著瞌睡。
迷迷糊糊间,听著钟响,听著佛唱,又听见床板“嘎吱”,以为天亮了,师兄弟过来换班。
一睁眼,脑袋上刚生出来的细发都嚇得根根竖了起来。
那瘦和尚,竟自个儿坐了起来,两眼直勾勾对著前方。
不知是喜是嚇,小沙弥哇哇大叫:
“活啦!他活啦!”
夹杂著佛音:
“诸恶虫辈,交横驰走。
屎尿臭处,不净流溢。”
……
“是朽故宅,属於一人。
其人近出,未久之间,
於后舍宅,忽然火起。”
“站住!站住!”
护法们连声呵斥,可法严全然置若罔闻,自顾自步步攀登。
周遭信徒纷纷看来,包含种种意味的目光让护法们如芒刺在背,更別说,钟声已响,意味著
祖师法驾即將出行,介时,若撞见这丑和尚拦在路上,叫他们如何吃罪得起?
无奈之下,哪怕是心里打鼓,也咬起牙。
“此乃祖师巡道,岂容尔等踏足?”
护法们飞身降下,大部看住城隍府一行,余下两员神將迅速出手试图扣住法严双肩,可指尖才挨著,都未及发力,便惊恐发现,一身降魔镇鬼的神力忽如泥牛入海消失不见,香火凝成的金盔金甲亦片片消解,暴露出法相下虚弱的魂魄。
临近的两员神將,乍见此幕。
“是何妖法?!”
惊惧之下,一个挥起了金瓜,一个砍出了宝刀。法严除却僧袍,身上別无他物,怎能抵挡神將兵刃?可非但城隍府袖手旁观,连他自个儿也不闪不避,眼看要毙命当场,那金瓜与宝刀却突兀自个儿偏转了方向,擦著法严掠过,击向了神將彼此,一个险些被砸烂了脑袋,一个差点被卸掉了臂膀,留著两双惊恐的眼睛仓皇对望。
其余护法早骇得散到两旁,目送著法严踩著钟声步步拾阶而上。
佛唱渐高:
“是时宅主,在门外立,
闻有人言:汝诸子等,
先因游戏,来入此宅,
稚小无知,欢娱乐著。”
“长者闻已,惊入火宅。
方宜救济,令无烧害。”
后山厢房。
瘦和尚人醒了,魂却好似没醒,不言不语的,瞪著眼就往外闯。
惊得小沙弥用尽了吃奶的劲儿去拦,他只穿了一件褌衣,屋外却天寒地冻,好不容易甦醒,再冻坏了如何是好?
沙弥只是个孩子,就算把自个儿掛上去,也阻拦不住,幸好闹腾动静招来作早课的师兄弟们,见著和尚醒来,且喜且惊都来帮忙。
可万万没想,和尚枯瘦的身体里似乎藏著龙象之力,十几个师兄弟连推搡带拖拉,也停滯不了他徐徐向前的脚步。
直到。
“住手。”
那是个老成一截枯柴的老和尚,他辈分很高,院里的和尚都唤他师叔祖,他叫眾僧散开,自个儿望著瘦和尚,不知为何渐渐泪流满面,他招呼弟子取来袈裟、串珠、法冠,为瘦和尚一一穿戴,不多时,儼然高僧模样,而后领著弟子们追隨著瘦和尚的脚步。
唱诵经文,亦步亦趋。
“诸子无知,虽闻父诲,犹故乐著,嬉戏不已。”
……
晨钟声声惊破长夜,佛光高炽照彻云霄。
轮转寺內金光漫漫,教一切阴暗污浊无所遁形。
虚空中,护法们纷纷显出法相,身放佛光,神威赫赫仿佛能扫灭一切魔障。可若能看破金光,瞧清他们脸上神情,便知他们个个慌乱得很。
无论现法相,还是放佛光,都非他们自己所愿,却是香火凝成的法身自行其是。过去仰仗著能逞威风、压人鬼的法身,忽然之间反客为主,摆弄著自己呼应著今夜寺中异像。
地上的僧眾更早已陷入惶恐之中,金光照耀之处,手中器具忽而都似有了生命,旗帜无风招展,乐器自行吹奏。偏偏又伴著佛音,天上坠下红白黄青四色莲,落在头肩,化为清凉流入心底,消除烦恼,生出依慕,忍不住隨著佛音唱和。
而妙心年纪最长,修行最高,感知到的也最多,他模糊察觉,经声不是出自僧口,却是来自於那九座供奉著金身的佛殿,这金光这钟响並非谁人所为,而是整个轮转寺在欢欣在雀跃。
可他却只能眼睁睁看著,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他身上由香火凝成的佛法神通亦是最重,过去,这佛法神通是他的华衣,是他的甲冑,是耳目,是手足,而今变作沉重的枷锁,將他死死定在了华贵的神轿上。
听著经声阵阵:
“以眾宝物,造诸大车,庄校严饰,周匝栏楯;
四面悬铃,金绳交络,真珠罗网,张施其上。”
……
所幸,这种折磨没有太久。
不多时。
从后院方向走来一群僧人,他们与广场上其他僧人不同,没那么衣衫华贵,没那么“宝相圆满”,只是普通和尚,唯有为首的一个,披著锦襴袈裟,戴著莲发冠,陪著七宝念珠,神情无悲无喜,儼然高僧模样,领著僧眾,缓步上前,念诵经文:
“一切眾生,皆是吾子,深著世乐,无有慧心。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眾苦充满,甚可怖畏。”
又见山门自行洞开。
遥见一僧,步步登上石阶,金枷银锁、夜游武判等阴司大神紧隨其后。
此僧衣著素寒,仪容潦草,似个乡野討食的苦行游僧。可步履间,莲乱坠,佛唱相伴:
“如斯罪人,常生难处,狂聋心乱,永不闻法;
於无数劫,如恆河沙,生輒聋哑,诸根不具。”
……
两方人马进入广场,各自驻足,
唯有那高僧与游僧,继续穿过茫然的护法、无措的僧人,彼此相向而行。
隨著两者渐近,金光愈加灿漫,浓郁犹如实质,钟声阵阵,在光芒里盪起水波,翻起涟漪作佛唱:
“告舍利弗,我说是相,求佛道者,穷劫不尽。
如是等人,则能信解。”
“汝当为说。”
很快,在场者眼里只见金光,耳中唯余钟声,高僧与游僧终於相会,最终,合二为一。
没有再添异像,也没有多增神跡,相反,佛光迅速沉降,钟声停了,佛唱也静了。
唯有广场中央,法严一声轻诵。
“妙法莲华经。”
……
金光既灭,僧人与护法们终於得了自由。
有对城隍府怒目而视,有对后来的僧人大声呵斥,但更多是迷惑,是惶恐,他们纷纷望向了他们的主心骨——端坐在神轿之上的妙心禪师,慌乱呼喊著“祖师!祖师!”
可挨得近,譬如宝光,却分明能瞧见妙心禪师珠旒之下目光散乱,口中反覆呢喃著一个词。
“祖师?”
……
“尔等愚僧好生蒙昧,对著个假佛假祖师磕头不止,见著真佛真祖师却反倒不拜吗?”
千年之前的縹緲传说走入现实,哪怕有金光、佛唱让轮转寺本身作出证言,却仍让人难以置信,一时瞧瞧佇立原地轻声诵经的法严,一时往往高坐神轿默不作声的妙心,僧人护法个个犹疑不定。
但很快,隨法严肉身而来的和尚们作了表率,齐齐伏拜,但其余僧眾大多不为所动,仿佛不是一路人。实则,確实不是一路,轮转寺中有两派僧人,一派是常住派,多是本土子弟,另一派则是歷代护送金身南归的僧人所传,被称作侨居派。
可紧接著,宝光天王为首的护法兵將亦齐齐下拜,恭称“法主”。由不得他们不拜,法严诵经声虽轻,可落在耳中,却字字如千钧之重加诸法身,压得他们不得不低下头来。
有了护法们带头,再加上妙心仍一声不吭,场中僧眾终於顶不住压力,陆陆续续伏拜叩首。
李长安长舒了一口气。
贏了!
昔日出海寻城隍印,是在不可行中挣一个可行,可真寻回了城隍印,就一定贏得了十三家?谁也不敢肯定。但当与法严在龙宫重复,交流了钱塘现状,得知其本来身份,道士便决定换个计划。要贏棋,与其捉棋子,何如捉棋手?十三家要不惜一切推轮转寺的妙心作钱塘城隍,如此甚好,咱们就夺了轮转寺!
而今计划成了大半,当务之急,是继续完成巡神的仪式。舞台既已搭好,真正的主角若不登场,岂不可惜。
正好天际泛白,事不宜迟,正要张罗巡行。
忽听得一片叩首里。
鏘。
李长安汗毛倒立。
那是刀剑出鞘声!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