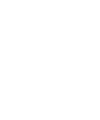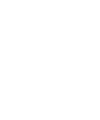万国之国 - 第333章 两处宴会(上)
第333章 两处宴会(上)
当站在雅法门前的时候,鲍德温不由得想起,这可能是他为数不多,不是让塞萨尔等着自己,而是自己等着塞萨尔的时候。
最初的一次当然就是塞萨尔结束了在圣墓大教堂的苦修之后,回到圣十字堡时,他在等待;之后应该是塞萨尔代自己去寻找,并且援救艾蒂安伯爵时,他期待着他能够安全的回到自己身边;第三次是则是塞萨尔去了伯利恒,但那也是一段短暂的日子;最后一次可能就是塞萨尔出使阿颇勒,当听说塞萨尔在大马士革遇险的消息时——那次他多么惊慌啊,他还是第一次真实的感受到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塞萨尔的,却要更可怕。
那时候他就在想,今后他再也不让塞萨尔离开他,离开亚拉萨路了。
虽然他也知道这不可能,塞萨尔是那样的勇敢,又是那样的聪慧,又如何能够因为一己之私而将他约束在自己身边呢?
哪怕塞萨尔也向他发过誓,如果不是他要塞萨尔走,塞萨尔绝不离开他。
但事实证明,孩童时的诺言总是终被长大后的现实所击破,在这之前,他从未与塞萨尔离别的这样久。
虽然相信塞萨尔绝非一个魔鬼,但教皇的大绝罚就如同一柄摇摇欲坠的利剑架设在他与塞萨尔之间,鲍德温数次都想要离开圣十字堡去见塞萨尔,但都被王太后玛利亚劝阻住了,这可能会让罗马教会认为他们狂妄到无视于他们的权威——塞萨尔的弱点在于没有基业,但也胜在没有基业,鲍德温则不同。
何况之前鲍德温已经做出了让旁人看起来颇有些过分的事情——他驱逐了安条克的大公博希蒙德以及的黎波里爵雷蒙,这两个人都是他叔伯般的长辈,是阿马里克一世没有血缘的兄弟,的黎波里伯爵雷蒙还是他的远亲——做过他的摄政大臣,而博希蒙德则是他姐夫的父亲,而他们所做的事情,从程序上而言并无可挑剔的地方。
无论是阻止他前往伯利恒——在瘟疫横行的时候,一个国王原本就不该让自己身处险境,还是让自己的儿子接管了大马士革——这里说的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
与塞浦路斯不同,大马士革可以说是十字军打下来的城市,当然不可能由一个罪人掌管,而在年轻的骑士之中,有这个身份、资格与功绩来担当起这个重任的,也不可能是个如亚比该般的废物。
而且大卫也是一个公认的好骑士,虽然事实证明,木桶那块短缺的木板确实会招来弥天大祸——但那时候人们一致认为他会是个很好的接任人选,就连塞萨尔也承认了。
但鲍德温甚至有些迁怒于大卫,以至于在有关于大马士革的会议上,他数次毫不留情的驳斥了雷蒙的要求——雷蒙希望他能够将大马士革封给大卫做领地。
鲍德温的想法很简单。当初在攻打这座城市上出力最多的,除了他就是塞萨尔——即便如此,塞萨尔也没有要求得到大马士革,而是建议鲍德温派驻总督,这样,大马士革依然属于亚拉萨路。
虽然对于亚拉萨路来说,它是一块飞地,但至少在宣称和权力上应当如此——其他人应该只是代鲍德温管理这座城市,是官员,而非主人。
这对于鲍德温和亚拉萨路当然是有利的,因此也得了到了不少支持者。但赞成黎波里伯爵雷蒙的人也不少,这主要涉及到了一个习惯法。
这里可能要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德意志诸国时常为了王位而大打出手,厮杀不断,作为两大有力家族的联合诞下的结晶,腓特烈一世是个毋庸置疑的战争爱好者,他有个绰号叫做巴巴罗沙,意思就是红胡子,这个绰号是他的宿敌,意大利人给他的。
正是因为他曾经两度攻占意大利,并且通过强大的武力手段,逼迫意大利人臣服,人们传说他的红胡子是血染的,并且用此来恫吓孩子。
而他也有着自己的盟友,其中最得他信任的应该就是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但此人却因为本身的权力与皇权的冲突而渐渐的失宠于皇帝,就是亨利二世去世之后(因为狮子亨利娶了亨利二世的女儿玛蒂尔达),腓特烈一世最终吹起了进攻号角,而在失去亨利二世这个有力的后台后,狮子亨利的军队在腓特烈一世面前一败涂地。
他的大部分领地都被剥夺,只留下了两座城市——腓特烈一世虽然对这些领地垂涎三尺,但为了表明自己只是为了惩罚狮子亨利对他的不逊,而并不是有意剥夺诸侯的领地——避免引起他们的恐慌,而将所有被没收的领地分给了其他公爵,而非没收为自己的王室领地。
这种做法固然慷慨,并且被人称赞为高贵——当然了,谁突然得了那么一大块领地都会这么说的——但这无形中给所有的基督徒国王立下了一条无形的规则,那就是被没收的诸侯领地,只能短暂的归国王或是皇帝。
君王们不能因为想要拓展自己的领地,而向诸侯们发起挑战。
因此,对于那些人来说,他们更支持的黎波里伯爵雷蒙的儿子大卫得到这块领地——他们认为,大马士革应当属于十字军而非亚拉萨路的国王,就算国王出力最多,也完全可以用其他领地交换,或是用收入补偿……
何况的黎波里也是四大基督徒王国中最小的一个,如果能够与大马士革连缀成片壮大它的力量,对十字军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何况大卫的英勇,虔诚,众人有目共睹,交给他也在情理之中。
亚拉萨路国王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与固执,被他们看做了少年人的不成熟,不稳重,或者说他们的某些想法或许正与博希蒙德或的黎波里伯爵雷蒙有着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并不乐见于国王身边多了一个可信、忠诚又得力的人。
而进一步让鲍德温停下脚步的是宗主教希拉克略的身体状况。
虽然在塞萨尔的药物与看护下,宗主教得以从死神的阴影下逃脱,但疫病确实对这位老人造成了一些伤害,他也一直在想办法,不过是借助亚拉萨路的权威,向罗马教会施加压力,而后用贿赂来说服那些红衣亲王——另外就是安排可信的人去保护塞萨尔,免得这些人进一步迫害甚至谋杀。
“怎么了?”
鲍德温回首问道,他隐约感觉到了周围有些吵嚷的迹象,一个骑士靠近他:“是一些平民,他们听说……塞浦路斯领主要进城,都来欢迎他……”
国王抬起头,发现和他这样做的不在少数,骑士说一些,这一些可未免太多了,他们畏惧士兵的长矛,不是躲在房子里,就是藏在巷道里,只能看见攒动的脑袋和在阴影里闪烁的眼睛。
原本鲍德温也是不将这些人放在眼中的——这些犹如杂草般的存在,能做些什么呢?
但就是这些渺小的存在,在他和宗主教都心焦如焚的时候,保护了他们爱着的那个人。
他们第一次看到了那些孱弱的躯体中所能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就连宗主教也不由得会跪在地上,仰望着耶稣基督的苦像,询问这个世上是否确实有着真正的善良,以及与之相等的回报呢?
可即便是在千年之前,人们回报给耶稣的,也不过是环与露水,但塞萨尔却能在那些贫贱之人那里得到堪比一个国王的帮助与庇护,在引得众人惊讶的时候,也无形中改变了一些人的认知。
他们的行事方式至少在亚拉萨路以及周边的城市中有所改变,贵族与骑士们已经不再那样肆无忌惮——品德高尚者,当然一如既往,那些残忍暴虐之人也不免和气了几分。
毕竟要说虔诚,他们也并不怎么虔诚,要说利益,就连国王也要与教会相争,何况是他们这些领主和爵爷呢——教会又不是第一次用绝罚来争权夺利?
他们甚至也动过免除一部分税款的意思,但随之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没法做到塞萨尔所能做到的那些——不建造城堡,不修筑宫殿,不穿丝绸的衣服,不饮醇厚的美酒,不用昂贵的香料,不办宴会也很少狩猎——除了那些用于补充宴会和节庆消耗的狩猎。
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一个领主,哪怕加上他的家眷,亲近的骑士和官员,又能够挥霍掉多少钱财呢?事实上,这还真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支出。
五百年后的一个国王身上佩戴的钻石甚至可以与一支舰队等价。
有时候也未必是这些领主过于喜欢华服珠宝,而是他们并没有与自己身份相称的礼仪与风度,为了凸显自己的身份,只能用这些浮夸的外物来炫耀和展示。
塞萨尔也曾必须这样做——他才来到圣十字堡的时候,鲍德温就将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但现在他已经不需要了,美德远胜过任何珠宝。
“智慧、仁义、公平、正直。”鲍德温不由得轻轻念了出来,将这些字镌刻在砖石上,是一件无比容易的事情,但若是想真正的把它放入心中,又是千难万难。
此时,正有一队骑士裹挟着滚滚烟尘而来。
一个目光敏锐的骑士已经低声道:“是英国人!”
理查一世举着的是圣乔治十字旗,旗帜以红色底色为主,中央会白色十字,从英格兰王室的三狮徽章演变而来。
“理查一世到了,陛下,请前去迎接。”贝里昂伯爵低声提醒道,在国王毫不犹豫的驱逐了安条克大公博希蒙德以及的黎波里伯爵雷蒙之后,原先身份尴尬的贝里昂便一跃成为了国王身边最可信的大臣之一。
而贝里昂并没有辜负国王的期望,他为人谨慎,这是一个弱点,也是一个优点,老成沉稳的性情,也成为了年少气盛的国王,与其他大臣之间的缓冲带,更不用说他的身后是国王的生母雅法女伯爵。
雅法女伯爵虽然之前与鲍德温起了一点小小的龃龉——鲍德温和希比勒都是她的孩子,她不可能因为爱着一个孩子而彻底舍弃另一个孩子,但希比勒又一次令她失望了,她不信希比勒对伯利恒的事情一无所知,希比勒也应该知道,塞萨尔对鲍德温有多重要。
为了弥补之前对鲍德温……或许还有塞萨尔的亏欠,贝里昂伯爵就成了鲍德温与塞萨尔之间的信使,虽然不能见面,但通信也能减缓鲍德温的内疚,还有担忧。
“他说会和塞萨尔一起来。”鲍德温热切地说。
英国国王可不是塞萨尔的侍从啊,贝里昂在心中说道。
幸好国王的话音才落地,就有另外一个手持着赤红旗帜的骑士疾驰而来,亚拉萨路十字架以及新月、八芒星。下方是“与主同在”的箴言,在看到这面旗帜,鲍德温的心才终于不那么焦躁了。
而这位使者也已经下马向国王行礼,并且通报了他们的主人即将抵达的消息。
这就是塞萨尔不是以一个十字军骑士,而是以拜占庭帝国的专制君主的身份前来的一个坏处了。
若他只是一个十字军骑士,一个空有名头的伯爵,鲍德温完全可以立即纵马上前,在途中便迎住自己久违的朋友,与他紧紧拥抱,一述别情。
现在,他若是迎上前去,将这场会面变成了不正式的,那就是对一位君王的不尊重。此时,他也只能按捺住一颗跃跃欲试的心,只想着是不是有什么拖慢了塞萨尔的脚程,才会让他等得的如此心焦。
确实有什么拖住了塞萨尔的脚程。
虽然罗马教会已经取缔了他的大绝罚令,但塞萨尔并未表现的如那些获得赦免的人那般欣喜若狂,也不急于去教堂忏悔、祷告、做弥撒。
他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未发生过那样,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而鲍德温也会意的——向塞浦路斯的领主,拜占庭帝国的专制君主,而非他的总管大臣和埃德萨伯爵递出了邀请。
塞浦路斯大主教很快将这个消息传播了出去,塞浦路斯上的贵族与民众无不为之欢欣鼓舞,竟然在短短几天内就拿出了一整套华美的仪仗,这速度快到塞萨尔都要怀疑这套仪仗是不是他们之前为大皇子阿莱克修斯准备的。
这套仪仗中包括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驮轿——是的,拜占庭的专制君主在正式场合并不骑马,教士手持着圣像走在前面,之后则是手持着银手杖的仆从,之后则是塞浦路斯的贵族,他们骑着马或者是踱步,速度一样的慢。
每个人都打扮的华美异常,身上的宝石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几乎连缀成一片耀眼的虹光,最让塞萨尔感到惊讶的是那座驮轿,这让他立即想起了拜占庭帝国的玛利亚公主曾经乘坐过的那座,它简直就像是一个小房间,但比起公主的那座,它的装饰显然要更为肃穆和庄严,四周都垂着紫红色的丝绒帷幔,每一处缝隙都填满了金子或者是银子,四角的雕像——从他们所佩戴的事物来看,应当是四个可敬的圣徒,将手放在胸前,眼睛则看向驮轿内,仿佛要为里面的人施加祝福。
而两面的镶板上则是塞萨尔的纹章——颜色艳丽而又纯粹,不必多说,这些颜料必是用了昂贵的矿石粉末,而承载着它的并非是常见的骡子啊,是两匹高大的黑色驮马。
最后还有十二名骑士,骑着毛色一致的褐色骏马随行——也不知道这些贵族们是如何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寻找到这十二匹颜色个头都十分接近的马儿的,这些骑士们无疑都是对塞萨尔最为忠诚的那些——头盔和链甲都镀了银,在阳光下,犹如一片涟漪层迭的水面。
在骑士们所持的旗帜投下的长长阴影中,跟随着一百名士兵,他们各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从皮带、靴子,甚至武器都是一个制式的。
在此时已经有了所谓的领主部队,而塞萨尔招募士兵的事情也没有隐瞒众人的意思,只是那时候人们也只会以为这是普通的农兵,顶多是半职业兵——但现在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是真正可以拿去打仗的。
他们在暗暗艳羡的同时,又期望这些士兵只有他们所看到的一百人或者是教会所要求的一千人——顶多了,如果再多一些的话……
“幸好安条克大公博希蒙德和的黎波里伯爵雷蒙不在这里。”一位爵爷幸灾乐祸地与同伴说道:“不然的话,他们准要心惊胆战。”
可以说,如果塞萨尔是个如大卫般,在教士们的教导和父权的压迫下长大的孩子,博希蒙德与的黎波里伯爵雷蒙所设下的这个陷阱,完全可以将他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现在他没受伤,没死,甚至看上去有着几分因祸得福的样子,可不是他的敌人高抬贵手,而是他之前积累的功德和他本身的坚韧——如果他真有一千个这样的士兵或更多的话,那两个人恐怕就只有期待对方确实如传说中的那样高尚,可以不计前嫌。
毕竟一个君王要惩戒自己的附庸,也必须考虑到其他附庸会不会兔死狐悲——但领主与领主之间的战斗却时常发生,有时候是某个倒霉的伯爵被抢走妻子;或是因为领地和水源的划分而产生冲突;更有因为农民在对方的唆使和诱惑下私自迁徙而大打出手的——就算是没有,难道还不能制造一两个吗?
也就是现在塞萨尔所有的是塞浦路斯,一个岛屿,与安条克,还有的黎波里都不接壤,而塞浦路斯的海军又未能完全成型——但这位塞浦路斯的领主是多么的年轻啊,在自己无可避免地步入衰老时,自己的敌人却正在盛年——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了。
只是当那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接近雅法门的时候,宗主教希拉克略不由得轻轻的嗯了一声,他觉得有些不对——因为另一股队伍,也就是打着英国国王旗帜的反而走在了塞浦路斯队伍的后面。
专制君主虽然位于拜占庭帝国阶级的第三列,也就是说,仅次于皇帝巴西琉斯与其下的共治皇帝,或者是“最显贵者”,但这个称号并不被罗马教会所认可,即便被认可了,也必然低于国王。
塞萨尔一向谦卑,随和,应当不会做出这种狂妄的行为,宗主教自认非常了解自己的这个学生,不会突然变成一个轻浮的纨绔子弟,他正转过去要和鲍德温说些什么,却见鲍德温已经飞驰而出,迎向那座抬轿。
他甚至没想到,就算塞萨尔没有骑着卡斯托,也必然会让它跟在驮轿旁,而伴随着一阵大笑,驮轿前方的帷幔径直飞向半空,一个魁梧的身影从里面冲了出来——那两匹强健的马儿都不由得微微一屈膝盖,几乎要不堪重负的倒下。
鲍德温抬起头来,难得的露出了茫然的神情,虽然逆着光,但对方的那头红发在空中飘扬着——仿佛一捧燃烧的正热烈的火焰——他当然能认出这个人,这不是塞萨尔……他还没来得及后退,理查长长的手臂就伸了出来,紧紧的抓住鲍德温,来了一个无比热烈的拥抱。
鲍德温今天骑的是波拉克斯,这匹与卡斯托一般强健无比的马儿在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后,也同样经受住了友谊的考验,它只后退了一步,便稳稳的接住了理查和鲍德温两个人的重量,只是不满的喷了喷鼻子。
如果不是还背负着主人,它准要给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狠狠一蹄子。
理查以这种别扭的方式恶狠狠地抱了鲍德温一记不说,还用力拍击他的后背,比起虽然高挑,但也强壮的塞萨尔,鲍德温要单薄一些,被这头人形巨兽猛得拍了这么几下,他只觉得自己头昏目眩,都快要吐了。
而此时,他听见波拉克斯发出了一声欣喜的长鸣,一个人正骑着卡斯托从理查的队伍中飞驰而来,他靠近了两人,一把就将鲍德温从理查的怀抱中抢了出来。
“谢谢,谢谢。”他代鲍德温说,“但够了,理查。”
理查坐在驮轿的踏板上,笑嘻嘻的看着两人:“怎么样,鲍德温,这算是一个惊喜吗?”
鲍德温没好声气地白了他一眼:“确实是个惊喜,都快变成惊吓了。”
波拉克斯朝理查卷起嘴唇,和主人一模一样,理查伸出手,里面有好几颗冰,马儿看也不看,反而朝他唾了一口,带着腥臭味的口水飞溅到了英国国王的身上,他却毫不介意,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原本庄重肃穆的迎接仪式被理查弄得一团糟,这位蹩脚的吟游诗人,勇武的骑士,不怎么负责任的国王,却丝毫不以为意,他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唾液,往自己嘴里扔了块冰,咬得咯嘣作响。
那些拜占庭人,还有他的随从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因为他们的国王还坐在塞浦路斯领主的驮轿上,而塞浦路斯领主却和亚拉萨路的国王并肩骑行,最后他们只能潦潦草草的混成了一大股队伍,就这么进入了城。
一个教士快步追上前来:“您实在太鲁莽了,陛下。”
“鲍德温不会在乎的。”
“我说的并非是这件事情。”修士用几乎微不可见的声音说道,“您没有看到吗?亚拉萨路国王脸上的红斑,他是个麻风病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即便直至今日他身边都没有遭到感染的人,但灾祸是如何降临的,谁也不知道。
您和他如此亲密,着实不应该。”
他不顾理查瞬间冷下来的脸色,“您已经是位国王了,就不该还如骑士那般任由自己的心意,胡作非为,即便不为了您,也应当为您的母亲,为您的国家,为您的子民多做考虑。”
“真奇怪啊,”理查仿佛自言自语般地道,“你们还指望琼安和他结婚呢,我以为你们不在乎他是个麻风病人了。”
他这么一说,教士无言以对,“那不一样。”
“那太一样了。”理查收起了笑容,幸好他已经回到了帷幔后,而教士是探过身体和他说的,他不必担心有人能够窃听得到他们的对话。
“我们还没提及这件事情呢……”
“但亚拉萨路的人一看到琼安,就应该猜到她是为什么被送过来的?你们不希望看到我和一个麻风病人拥抱,却愿意将我的妹妹嫁给一个麻风病人。”
“陛下,这也是埃莉诺王太后的意思,琼安公主也答应了。”
“她又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她被我的父亲嫁给西西里国王的时候,也没人征询过她的意见。”
“这是一桩荣耀。陛下。这里的法律允许王后参与政事,即便她未能生下国王的继承人。而且埃莉诺王太后如此做,也是为了……”
“别说了!”
理查烦躁的打断了对方的话,虽然对于鲍德温来说有些愧疚,但他已经决定了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对塞萨尔以及鲍德温坦诚,并且恳求他们的原谅。除了对这个小妹妹的责任和关爱之外,也是因为这两位骑士的高贵品质不应当因此受到玷污。
理查将妹妹琼安带到这里,也是迫不得已。
他在启程的时候才知道,在西西里国王去世之后,他的堂兄坦克雷德便毫不犹豫的以堂弟无嗣为理由,攻占了他的城市,掠夺了他的王位,并且软禁了他的妻子,也就是亨利二世的女儿,理查的妹妹琼安。
琼安是65年生人,76年才与西西里国王结婚。
而在这短暂的婚姻中,她没能为西西里国王生下孩子——当理查要求坦克雷德归还自己的妹妹,以及她的嫁妆时被拒绝了。当然,这位好战的国王没有继续谈判的意思——他立即便指挥着自己的军队,用刀剑来说服这个卑劣的小人,甚至宣称他不介意先打下西西里,迫于无奈坦克雷德才将琼安与她的嫁妆归还。
理查原本想要派一部分人将琼安送回英国,却被随行的教士劝阻,教士说,在一桩失败的婚事之后,公主能够前往圣地朝圣,并且在那里修行上一段时间,或许会有利于她之后的婚事,直到抵达了阿卡,不可能再将公主送回去了,才向他坦言道,埃莉诺王太后想要将琼安嫁给亚拉萨路的国王,从身份和年龄上来说,他们都很匹配。
琼安比鲍德温小五岁,一个是国王,一个是公主,而理查又曾经与鲍德温并肩作战,他们之间的友谊,甚至要比理查和腓力二世的更深厚些,而且理查一直将为天主作战,是做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如果有一个亚拉萨路国王做妹夫,对他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理查可以与鲍德温成为朋友,为他献出生命也不是不可以,却很难亲眼看着妹妹走入另外一段没有结果的婚姻。
问题是这桩婚事甚至由不得理查,又怎能由得了琼安呢?
她还是那样的年轻,在得知自己可能会被嫁给一个麻风病人后,心中必然充满了不安与忧虑,但她同样没有违抗自己母亲的勇气和意愿。
宴会开始的时候,当人们得知英国国王的妹妹,新寡不久的琼安公主也来到了此地时,那各异的神情与窃窃私语声,更是让她坐立不安,她甚至没有勇气抬起头来去看一看,那个可能成为她未来丈夫的人的脸。
她在布施的时候也曾经见过那些因为麻风病而溃烂肿胀的面孔,多可怕呀,那简直就是一个被强行称之为人的怪物,她无法想象自己将来要与这么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甚至到了坟墓里,他们也要一同长眠。
如果她的丈夫是塞浦路斯的领主该多好啊。
随即她便将这个亵渎的念头按了下去——她也在游行的队伍中,这位君主不但容貌俊美,身形颀长,还有美好的品德与温和的性情——那些喊着“小圣人,圣人”的人群的眼神她是不会看错的,他确实受到了这些人的拥戴,甚至超过了亚拉萨路的国王。
但她之前受过的教导,是要爱自己的丈夫,如同爱着天主,也要对他保持应有的忠诚,更不用说塞浦路斯的领主已经是一个有妇之夫,他与他的妻子同样在天主的恩曲与众人的祝福中缔结婚约,也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但想到这一点,她又不由得浑身颤栗。她与西西里国王的婚姻中,事实上是曾经有过一个孩子的,只是这个孩子还未命名就夭折了——因为没有经过洗礼的关系,这个孩子的死亡意味着他的罪过无法被洗脱,所以也不再有人提起。
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健康的女性来说,不渴望自己的孩子是不可能的。可若是嫁给了一个麻风病人,就意味着他们永远不可能有孩子,她当下心下惶恐,如果不是还有作为一个公主的骄傲支撑着她,或许她真的要当场昏厥过去了。
(本章完)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